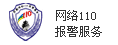管理风格
特质理论倾向于研究领导者的内在个性特点,行为理论则重点解释领导者的外在行为特征。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和简·默顿(Jane Mouton)提出管理方格理论,以“关心生产”和“关心人”为坐标,将领导者的管理风格主要划分为四种类型:贫乏型、乡村俱乐部型、权威型(血汗工厂型)、团队型(全功能型)。
从中国企业30年的实践来看,一部分企业领导者似乎更关心人,对应“乡村俱乐部型”风格,特别是家族企业、乡镇企业、校办企业或“哥们企业”。但实质上,他们不是真正关心人,而是关注人际关系和人情,其管理风格更像“江湖好汉型”,不属于商业管理范畴。还有一部分企业领导者极其关心生产,漠视人的存在,把企业办成了“血汗工厂”。他们关注的是“短期利益”和“真金白银”,而不是企业的战略和发展。更多的领导者陷入贫乏型管理的泥潭,致使企业无法突破甚至难以存活。
其实,类型划分是为了学理上的便利,而领导力的行为特征一定是“人”与“事”的结合,而“组织”是二者结合的天然平台。与西方管理者不同,中国企业领导者不仅要同时关注人与事,处理二者的平衡;还要建立组织平台,推动企业从个人化转向组织化。中国既缺乏真正的职业人队伍,也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和规范。30年来,为了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付出了比西方企业更大的代价。
在艰苦的实践过程中,优秀的中国领导者逐步探索出一条有效的管理路径和组织演化进程。首先,格外关心事,以事为中心,强调任务导向、目标导向和成果导向,以此冲击和打破“主人翁”的政治角色意识;在此基础上,加大对人的关心程度,但重点是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机制,引导、激励人做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人与事的平衡达到一定基准后,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即使最优秀的中国企业,也远未达到“人为本”的境界。从本质上分析,优秀领导者自始至终是团队型管理风格,只是阶段性表现不同而已。
任正非受人非议的焦点,就是“床垫文化”、“狼性”、“过劳死”等特性和事件,华为甚至被有些人视为“血汗工厂”。平心而论,无论是对人才的重视与激励程度,还是对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力度,华为在中国企业界无出其右。《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更是把任正非的铁汉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竞争惨烈的通讯设备领域,在核心技术严重匮乏的高科技行业,在组织的特定阶段,看似残忍的绩效导向其实是“不得不”的理性选择,这正体现了任正非对“人、事”平衡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柳传志“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的三段论,也是人与事平衡思想的生动体现。在杨元庆、郭为的接班人问题上,在退出IT服务、并购IBMPC业务的战略举措上,这种思想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王石则一直强调做事的规范与人的职业化,始终保持“人”与“事”的均衡发展。从反面来看,那些不注重平衡的领导者,大多无声无息或昙花一现。
行为动机
行为特征表现各异,决定行为的深层动机又有哪些共性特征?借鉴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的理论,领导者动机是三种动机的组合,即权力动机、成就动机、亲和动机。中国人天生不缺乏亲和动机,因此,我们着重分析中国企业领导者的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
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强的领导者,关注的是把事情做到最好,通过做事达到个人成功,落脚点在于事情本身和个体角色,企业只是实现个人成就的平台或工具。成就动机强的领导者,一般表现出较强的技术导向及专业倾向,最典型的是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和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
权力动机
此“权力”并非中国传统语言体系中的“权力”,而是指领导者通过影响和带动一群人来达成更高目标,关注点在组织和目标上,特别重视组织的构成、建设、发展、变革。权力动机强的领导者,不是将企业作为实现个人抱负的载体,而是把企业组织作为承载和创造价值的主体。《基业长青》中研究的企业家大多属于这一类领导者。
我们选择的三位标杆人物,其权力动机普遍较强。无论是王石、任正非还是柳传志,都不是所在行业的技术专家,但都拥有无以伦比的个人权威,凝聚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推动企业做强做大。他们并非没有成就动机,只是很大一部分转化为权力动机;其成就感的满足并非直接来自个人工作的体验,而是间接来自组织发展、人才成长、社会贡献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入模子”,是柳传志投入精力最多的事。为了“组织”的成长和延续,他不惜“下狠手、开杀戒”;任正非总是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华为基本法》的出台,西方管理的强力引入,以我为主的国际化策略,无不闪烁着他对组织思考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