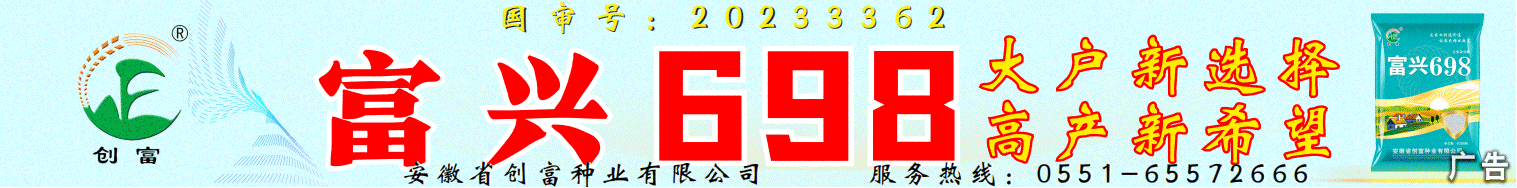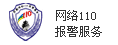石斛育种培养室内,工作人员查看石斛种苗的生长情况。新华社记者 郭程摄
种业,是种植业的根本,与国家的粮食安全息息相关。今天和未来的种植业增产越来越依靠良种的选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未来国际粮食总产增长的20%依靠播种面积的增加,80%依赖于单产水平的提高,而单产增加的60%~80%又来源于良种的科技进步。
然而我国育种行业的整体水平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解决“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现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关系到政策导向、科技水平和企业实力等方面。那么,我国育种科技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主要在哪里呢?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傅向东。
记者:我国哪些种子需要大量依赖国外?
傅向东:从主粮上看,我国的育种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在主粮育种方面持续投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良种繁育和推广体系,主粮保供能力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从非主粮上看,我国育种水平与国外差距较大,比如高端蔬菜、花卉、畜禽、草种等优良品种核心种源大部分掌握在国外公司手里,依赖国外进口。
记者:我国育种科技与发达国家相比主要差距在哪里?
傅向东: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育种上的科技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特别是功能基因的挖掘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创新上。基础研究是根本,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才能带动下游产业链。
我是从事水稻研究的,就以水稻为例。人类驯化水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随着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合成生物学等的发展,从“经验育种”到“精确育种”,设计“未来水稻”成为可能。比如某种野生水稻具有抗病耐逆优良特征,但是它容易倒伏、籽粒含淀粉量不高、食味差、产量低等。以前若想把野生稻的抗病耐逆基因转入当前主栽品种为我们利用,通常需要少则8至10年,多则十几年,一代一代连续回交转育,最后得到我们需要的改良品种。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基因编辑和从头驯化等育种新方法,将这些需要的高产、优质、抗病、耐逆等优良性状组合在一起,精准定制出我们需要的良种。这个过程大概只需要两三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功能基因挖掘和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在生物育种科技创新上的差距主要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从功能基因的识别上看,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已经识别出了很多作物的许多重要功能基因,并都申请了专利。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使用了某些别人已获得专利的基因进行育种和推广,就要付给人家钱。还有就是基因编辑技术,通过什么手段去改造基因也是一种专利。如果没有自己的基因编辑的核心技术,就相当于自己不能掌握生物育种的工具,也会被人“卡脖子”。
记者:该如何弥补这种差距?
傅向东:从科技产业本身看,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做基础研究,鼓励原始创新。一是要把国内的种质资源保住、保好,又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引进国外的优异种质资源。有了种质资源,才能有后来尽可能多的功能基因识别。我们应该多建几个种质资源库,并利用好现有的种质库,把种质库变成基因库、变成优良性状库。二是要吸引和鼓励生物、农业科研人员,加强优异基因的发掘与育种利用,并积极申请专利。这样才能把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是要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基因编辑技术的创新,加大投入去建立变革性育种技术新体系,把育种工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解决育种企业与基础研究脱节的问题。我从事育种的这些年里,很多工夫都花在和育种企业的磨合上。一方面,很多企业不知道基础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不了解,也不完全信任我们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不少企业缺乏长期的发展目标,不想投入经费和研发力量加速育种技术升级换代,只想做外来种子的“收购商”“代理商”和“销售商”。我想,这也是中国科学院要求我们做生物育种工作,并启动了相应先导专项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以我国当前育种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需求为导向,让基础研究“沉”下去,使基础研究与育种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科企合作,使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也随着一些育种企业认识不断地提高和实力的壮大,我们的分子设计育种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也希望企业能够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研发队伍,加强育种投入,加强技术的创新储备。现在经常有人说“中科院的像农科院的,农科院的像中科院的”,我觉得不能把基础研究与育种实践割裂开来。基础研究需要,也必须去解决育种实际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尤其是“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而育种实践中的重大需求又孕育着重大的科学发现。这应该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历史任务,需要我们上下游各司其职,通力协作,把我国的基础研究做好,进行更多的原始创新。当然,这是个系统性问题,需要国家顶层设计、政府相关部门、企业,金融业、科技界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记者:您对未来的育种科技有哪些展望?
傅向东: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吃得饱”的问题。下一步,育种应该瞄准“吃得好”和“吃得健康”的目标,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现代生物技术加速动植物新品种选育步伐,我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努力。比如,我们培育出抗病的品种,就能减少农药的使用,农药用的少了,就可以减轻土壤污染和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再比如,未来的育种很可能会和康养产业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针对糖尿病人的需求,培育低糖高纤维或者高抗性淀粉的作物品种,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再比如,随着信息技术、遥感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育种会更加数字化、定制化和智能化。每个地区的自然禀赋不一样,可能适合的种子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应用数字模拟技术,将这一地区的土壤、气象、光照、水文等情况与生物育种结合起来,精准设计和创造出适合这一生态区需求的种子。当然,传统的育种手段也不能丢弃,新品种不可能在电脑上设计、在实验室中长出来后,就一定能种植成功的。育种新科技必须和传统育种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育种行业必须关注到这些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做好科技储备。我国植物科学领域研究水平与国外相差不大,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科学家回国,人才越来越多,我们在国际上也有了较大、较强的影响力。
应该说,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和发达国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错过了这个重要的窗口期,未来几十年还会落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就能迎头赶上,把种子的未来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来源:光明日报 记者 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