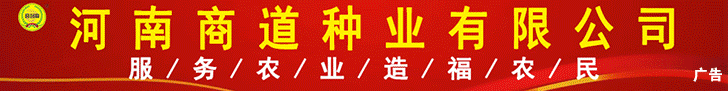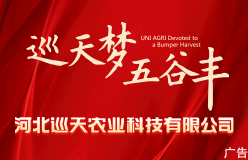(袁隆平,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张杰/图)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05月24日第1215期,作者:向郢,原题为《袁隆平:像野稻一样自在》
上周有一个重要的记者见面会,袁隆平的秘书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一个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
学农的原因很简单。还在读一年级时,老师曾带他们参观了汉口郊外一个私人园艺场。都好多年了,他始终惦记着,“里面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开得特别好。”
而重庆8年,有他最优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袭警报拉响,学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个兄弟姐妹,父亲喜欢老大,母亲喜欢老幺,成绩最好是老四,我这个老二就落在了空档里。”
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哪个理论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他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
家庭成分本来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能躲就躲,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农村上夜校,他讲红薯高产,听的人少,别的老师讲水稻高产,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农民跟他说,“红薯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吃了不经饿,‘以粮为纲’,是要大米。”
他后来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红薯”试验很短命。第二年,种子长出来,红薯又变小了。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亲曾是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直接上过外籍老师一年半的课。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